马上注册,结交更多好友
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账号?立即注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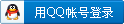

x
天津博物馆供图
本报记者 龚相娟摄
3000多年前,商代先民不仅创造出以甲骨文为代表的成熟文字系统,还在手工业领域取得了非凡成就,制作出一系列连今人都为之惊叹的精美产品,形成了高度专业化的官营手工业体系。这一体系以青铜铸造为核心,涵盖建筑、制骨、烧陶、琢玉、造车等领域,奠定了后世手工业发展的基本范式,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留下不朽篇章。
日前,“商邑百工——三千年前的中国制造”在天津博物馆开展。这是国内首个聚焦商代晚期殷墟手工业成就的专题特展,由天津博物馆和殷墟博物馆联合主办,包括“百工通览”“营造商邑”“器用皆工”“制礼作乐”“车马交通”五大单元和一个独立小单元“大商制造:牛”,共展出180余件(套)商代文物,涵盖手工业成品、半成品、原料、生产工具等,生动展现了3000多年前“中国制造”的繁荣景象。
巧妙组合,提升观展体验
未进展厅,展览已开始。走廊墙上的展板梳理了近百年来殷墟考古的主要成果,让观众了解展览的背景知识。
殷墟博物馆“镇馆之宝”亚长牛尊是展览第一阶段亮相的“明星展品”。它的对面是一只“小牛”——天津博物馆藏牛形玉饰。一个是盛酒的青铜器,一个是装饰用的玉器;一个是出土文物,一个是传世精品。“我们特意将这两件文物面对面摆放,让同一时期的瑰宝跨越3000年后实现对望。”天津博物馆书画研究部馆员、本次展览策展人之一张夏说。
一组“小与大”的对比颇有意思。河南省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收藏的带盖小铜鼎是迄今发现最小的商代青铜鼎,高度和重量与一枚鸡蛋相当。小鼎上方的展板印有现存商代最大青铜鼎后母戊鼎(曾称司母戊鼎)的图片。据介绍,后母戊鼎的高度是带盖小铜鼎的26倍,重量是它的近1.7万倍。
后母戊鼎是商王祭祀用的“国之重器”,代表了商代手工业的最高水平。带盖小铜鼎则是商代贵族儿童的随葬品,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纹饰、工艺都遵循商代礼制标准。既能做雄伟的大鼎,又能做精巧的小鼎,商代工匠的技术实力让人赞叹。
展览中展示的商代甲骨,蕴含着“点题”或“拼词”的巧思。“百工通览”单元展出了3片刻有“工”字的甲骨,“工典其幼其翌”卜骨刻于晚商帝乙、帝辛时期,其中的“工”字和今天的“工”字形态几乎一样。“营造商邑”单元挑选出分别刻有“商”和“邑”字的甲骨进行展示。“制礼作乐”单元并列展示了两片甲骨:一片刻有“鼓”字,该字所从之“壴”为鼓之形,所从之“攴”形似以手持棒,两者组合表现击鼓;一片刻有“舞”字,表现了一个人手里拿着舞具、双脚跳动的形象。两个字拼在一起组成“鼓舞”。张夏说,击鼓而舞最初是某种礼乐仪式,后来演变为一个词“鼓舞”,表达激发、振作之意。
策展团队通过文物之间的巧妙组合,让观众看展时能收获更多的信息和乐趣。“我们看到的不是孤零零的文物展示,而是自带话题的组合,这样很有趣,让人忍不住想拍照分享到社交媒体。”一名从北京来观展的高二学生说。
古今相通,体现文脉传承
展览中有不少具有生活气息的物品,让人感受到文化和技艺的千年传承。
“器用皆工”单元展出了3000年前的“搓澡神器”——陶(左爽右瓦)。此器为圆形,灰色,表面粗糙,有绳纹。硬底软面的设计和现代的搓澡刷相似,兼具实用和美学价值。
龙首纹玉觽堪称“解带神器”。玉觽一端为龙首,嘴部带一圆孔,供挂配之用,器身刻纹,整体向内弯成角状,尾端尖,用以解绳结。“古人系带容易打成难解的结,所以制造出带尖头的器物把带子挑开。到了现代,类似的工具依然存在,如冰鞋的鞋带钩、紧带器等。”张夏说。
亚址铜方尊让人联想到现代的乐高积木。它最大的亮点是肩部四角各有一个圆钉头,其上可套象头,肩部四边中部也有4个圆钉头,其上可套似鹿的兽头。这些兽头单独铸造,通过类似榫卯的结构与铜尊本体连接,方便装取,这种工艺在商代青铜器中较为罕见。
“商代采用范铸法铸造青铜器,难以在铸造器体的同时一体铸成结构复杂、纹饰精细的装饰性兽首,所以工匠采用了分铸法,先铸好兽首,再套到铜尊肩部已铸好的榫头上,还能随时拆下来把玩。”张夏介绍,这件青铜器设计巧妙,此次展览是它首次走出殷墟博物馆。
除了文物,展板上的内容也很有看点。殷墟出土的竹篓照片吸引了记者注意。这只竹篓1990年出土于郭家庄墓地160号墓,出土时放置在铜尊腹内,考古学家推测它是用来过滤酒糟的。
“根据殷墟M303墓葬中铜折肩尊出土时覆盖的浅褐色短梗南蛇藤植物层判断,商代人已开始饮用药酒。铜尊可能是专门用来盛放这种酒的容器。”张夏说,“商代的酒质量不如现代的精酿,杂质较多,所以古人用细密的竹篓来过滤杂质,这和现代人用滤网过滤咖啡渣是一样的。”
文物互证,还原历史细节
出土文物与传世文物的“互证”也是此次展览的亮点。传世文物经历代收藏、研究,流传有绪,但可能因为缺失“原生语境”(如使用场景、时代背景等)而导致“张冠李戴”“郢书燕说”;考古发掘出土的文物保留了墓葬、遗址中原始状态的一手信息(如摆放位置、共存器物、相关遗迹现象等),有助于补全传世文物的“出生档案”。“互证”是将两方面的材料结合起来,互相补充、印证,以全面还原文物背后的历史文化信息。
“器用皆工”单元展示了天津博物馆藏龙形玉玦。龙首微昂,张口露齿,龙身以“双阴线刻”工艺雕琢出勾云纹,刻工精细。这是一件传世品,单独来看无法确定其等级与用途。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同类型玉器恰好可与它进行比照:玉料材质、纹饰形态和疏密、刻划力度乃至表面的沁色都极为相似。通过两者互证,可以确定这一传世的龙形玉玦是商代高等级贵族用器。
“祼祭”展柜中,天津博物馆藏传世乙亥铭玉柄形器、鳞纹玉柄形器,安阳博物馆藏商代玉柄形器、父乙车徙铜觚,与展板上的文物线图、铭文等共同还原了商代“祼祭”的完整场景。
张夏告诉记者,“祼祭”是商代“人神沟通”的重要仪式。专家根据商代青铜尊上所铸的“祼祭”形象和考古出土的“玉柄形器+觚”的组合,结合“内史亳丰同”铭文、玉石铭文等资料,推断出玉柄形器是“祼祭”所用之“瓒”,觚是“祼祭”所用之“同”。瓒和同的制作都需遵循严格的标准,反映了商代手工业与礼制体系的深度融合。
天津博物馆藏铜铙和殷墟M303墓出土的马危铜编铙,分别展现了两个商代贵族家族对礼乐文化的尊崇;安阳孝民屯出土的商代禁范和天津博物馆藏西周夔纹铜禁,实证商周之际的文化传承……一件件精美器物,不仅体现了古人的匠心和技艺,还串联起一脉相承的文明发展轨迹。
围绕此次展览,天津博物馆组织了一系列专家解读活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原站长、南方科技大学讲席教授唐际根为观众带来一场精彩的导览,通过对器型和纹饰的深入解读,阐释了商代先民的工匠精神与思想信仰,让观众体会到中华文明的薪火相传、生生不息。(记者 龚相娟)
《人民日报海外版》(2025年09月30日 第 07 版)
|  /1
/1 
 扫码添加微信客服
扫码添加微信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