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注册,结交更多好友
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账号?立即注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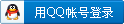

x
图①:顾棣在查看底片。
图②:在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顾棣与自己1945年的照片合影。
图③:1949年冬,顾棣在北京整理开国大典的影像材料。
图④:顾棣拍摄的1945年阜平城关春节的景象。
图⑤:1944年,顾棣(前排左二)与晋察冀画报社战友合影。
本文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80多年前,抗日战场上,战士们的武器各有不同,大炮、机关枪、步枪、刺刀……为了民族解放事业,什么都可能成为武器。
但老兵顾棣,在战场上时,手里的武器不能直接杀鬼子;抗战胜利后,又守护了80年,直到今年4月去世时,身边依然摆得满满当当。
他的武器,是相机,是底片,是守护了一生的档案。
岁月磨洗中,这些武器越来越亮,越来越有威慑力。
一场偶遇改变人生
“摄影记者用照相机打仗”
1928年,顾棣生在河北阜平县凹里村。历史选择了阜平,选择了凹里村,也选择了他。
阜平,1925年就建立了中共党组织,1937年以阜平为中心创建了我党我军历史上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这里长期是晋察冀边区党政军的首府和中心,聂荣臻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曾在此战斗生活过。
凹里村,隶属史家寨乡,晋察冀军区、晋察冀边区政府及各机关都曾在史家寨驻扎。
顾棣,父亲是村动员会主任,母亲是妇救会主任,兄长参加了抗日先锋队,他自己9岁时就成为村儿童团团长,后来成为阜平县一区儿童团团长,还被派到华北联大群众工作部培训。
但在顾棣的记忆中,直接改变他命运的那个人、那件事,出现在1943年。
那天,顾棣放学回家,离家还有七里地。路上,一个人骑着马迎面而来。那人身上挎着一个小盒子,带着一把手枪,开口问他:“小鬼,你到哪去?”
顾棣回答,自己要回凹里村。两人正好同路。
那时他还不知道,眼前这个人是中国革命摄影事业的开拓者之一沙飞,时任晋察冀边区政治部新闻摄影科科长、晋察冀画报社主任。
一路上,两人聊了许多事。
沙飞问顾棣,现在敌人经常扫荡,老百姓生活苦不苦、害怕不害怕?已在华北联大等学校学习过,对《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熟稔于心的顾棣,回答得胸有成竹。顾棣后来深情回忆起当时的场景:“我给他说,现在咱们抗日战争正处在相持阶段,困难是暂时的。沙飞听完就说,‘好,这么小就有信仰、有革命经历了。’”
一番攀谈后,沙飞起了爱才之心。两人聊到以后想做什么,顾棣说想演戏,沙飞却说,跟着我学摄影吧。“我就问,那是什么乐器,好不好学?”
沙飞取下身上的小盒子——一台盒式相机,一点点演示给顾棣看,镜头、取景框、胶卷……“他说,‘你看见什么就能照见什么’。他还说,‘战士用枪打仗,摄影记者用照相机打仗,把各种战斗场面拍成照片进行展览’。”
一年后,按照两人的约定,沙飞派人通知顾棣参加摄影培训班。刚刚成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的顾棣,毫不犹豫报名加入。
“1944年9月17日,我正式参加了八路军。”对顾棣来说,那天同样难忘。
顾棣的学生、人民摄影报原总编辑司苏实给记者发来两张老照片。那是刚刚接触摄影之后不久,顾棣在赵银德指导下拍摄的照片。时间是1945年2月13日,农历大年初一。在这一天的日记中,顾棣做了详细记录——
“忽然间从西街走来一支队伍,前边是锣鼓乐队,后面跟着村干部和男女青年抗日先锋队,队伍整齐威武而雄壮,最后是由小学生组成的霸王鞭,边走边打边歌边舞……”
仅这一天的日记,就有800多字,新闻要素齐全、现场刻画生动。其实,从1940年2月当儿童团长起,他就有了写日记的习惯,一直坚持到生命的最后,总量接近500本。
但那时只有17岁的顾棣,或许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记录、整理方面才能卓越,满心以为即将拿起相机,就像老师沙飞、石少华他们那样,奔走于战斗的前线。没想到,沙飞指定他从事摄影底片档案保管工作。
血气方刚的顾棣很不情愿。那个阶段的日记本里,常有不能上战场的苦闷。最终,沙飞一句话将他留在了岗位上:“这是命令!”
图片是历史的铁证
“人在底片在,人与底片共存亡”
当快门与枪炮声交织,对于用影像定格战场的摄影师来说,危险无处不在。
沙飞对此一清二楚,一位又一位摄影师在前线倒下,还有不少同志为保存底片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据不完全统计,晋察冀画报社的牺牲人数多达近40人。
图片是历史的铁证。如此珍贵的民族记忆,让沙飞为晋察冀画报社定下一条铁律——“人在底片在,人与底片共存亡”。这句话,影响了顾棣一生。
1948年12月,病榻上的沙飞依然给顾棣去信叮嘱:“这些东西也是全体同志10余年来血汗换来的结晶,所以我们都要加以爱护……”这封信,顾棣一直留着,直到2015年郑重捐给中国国家博物馆。
面对档案工作,顾棣很快展示出独有的才华。他忠于职守、细致认真、责任心强。
位于阜平县的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第三展厅里,展示着顾棣曾用过的许多物件。其中之一是,1945年在张家口缴获日军底片袋之后,顾棣受其启发制作出的红色底片袋。后来,解放军画报社一直沿用下来,将40多万张底片保存在这样的底片袋中。
为了保存档案,顾棣和战友们进行过诸多探索。更为重要的是,顾棣真的做到了将底片视作生命。他将底片进行详细编号和记录,背着、带着,跟随部队南征北战,从抗战时期的晋察冀画报社到解放战争时期的华北画报社,一直到后来的解放军画报社。他是解放军画报社第一任资料组长。
在军队,顾棣做了整整15年档案工作。
除了从沙飞手中接过的2万多张底片,他还四处搜集照片。1948年,华北画报社成立后,新增了前后方工作组的底片与人民画报社带来的3000多张底片,还有《冀中画报》停刊后上交的数千张底片;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绩展览会上,他与同事们一起翻拍了全部2000余张照片;1951年,收集近300张延安时的照片;1955年,陆续收到近十个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寄来的照片……
1958年9月,顾棣服从组织决定,转业到山西。此时,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照片底片已全部被编辑整理清晰、保存安全,并建立起严格的管理制度。直到现在,它们还被完好保存在解放军画报社,沿用着顾棣当年的登记编码存档方式。
顾棣收集的资料从晋察冀边区扩展到全国解放区。
为中国红色摄影修史
“我完成了这一任务”
司苏实还记得,那是2007年,老师顾棣的长子顾小棣向他“诉苦”,父亲生平第一次冲他们兄妹发了火。
那一年,一向身体很好的顾棣动了心脏大手术,一度情况十分危急。手术之后,他感到很虚弱,以为自己时日无多,忽然变得很脆弱。司苏实听完,立刻明白了:“他有事没做完,沙飞的使命还没有完成。”
这个使命,可以表述为,做一部完整记录中国红色摄影史的大型工具书。
当年,交到他手里的不光是底片,还有一份中国摄影人对中国革命事业沉甸甸的责任。顾棣多次谈到,中国摄影家协会成立50周年时,评选出10名“中国摄影大师”,其中有沙飞、石少华、郑景康、吴印咸4位给自己做过老师。
2007年,顾棣身体稍见恢复后,司苏实来到他家中。两人谈话时,司苏实告诉他,在沙飞女儿王雁建议下,自己已经决定全面介入这份工作。顾棣高兴地说:“这可解决大问题了!”
最终,在王雁策划、联络、协调下,司苏实作为特邀编辑,历经两年时间,帮助顾棣完成了由120余万字、1600多幅照片构筑的《中国红色摄影史录》。
司苏实那几年经常陪着顾棣外出。他记得,完成此书后,顾棣“不顾重病之身和80岁高龄,一定要亲自进京去见战友、老师、领导,向他们汇报:‘我完成了这一任务!’”
其实,在这本集大成之作完成前,几十年间,顾棣从未停止对档案的整理与出版,已经与他人合著、参与编写了有关中国解放区摄影史、文艺史的六七部书籍。此外,他还写过大量文章,参加过众多相关活动。
顾小棣对记者感慨,父亲一生没有别的爱好,就是爱收集、整理、考证那些摄影底片和史料,撰写有关摄影史的著述。
2012年,顾棣荣获“第九届中国摄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颁奖语评价顾棣,“用完整坚实的大批文献档案为中国摄影留下一部严谨、翔实的有关中国革命战争年代的摄影断代史,成为前无古人的扛鼎之作。这也使他由一名摄影史料的保护者成为一名历史学者”。
但顾棣这样评价自己:“作为经历者、见证者、研究者,不把历史留存下来、精神传承下去,实在心有不安、说不过去。”
将一生所藏慷慨捐出
“其行感人至深”
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资料科科长栗静还记得,2008年的一天,还在担任讲解员的她接待了一位挎着相机的老人。老人在参观纪念馆过程中,“把几乎所有照片都给我们介绍了一遍,从照片的拍摄者到背后的故事,但他讲的很多东西我们根本不知道”。
从此,栗静开始频繁接触顾棣。她掰着指头算,至少与顾棣见过20次,也因此感触尤为深刻。
2014年,栗静受邀在北京参观了“顾棣从影70周年特别展”。这次展览,让她深受震撼,“没想到他手里有那么多资料”。
就在这次展览后,国家博物馆找上门来,顾棣欣然打开自己的收藏。最终,773幅晋察冀时期的原版照片、《晋察冀画报》合订本、沙飞写给他的信等珍贵文物被选中。然后,他又认真编写出晋察冀摄影工作者分布情况,以及87位摄影干部的简历档案2万余字,并作为顾问协助编辑完成《晋察冀抗战摄影集》。时任国家博物馆馆长吕章申感慨:“其行感人至深。”
不过,司苏实记忆中捐赠的场景,还有一个意外的画面:在将这些守护了大半辈子的珍贵文物捐给国家之后,顾棣当场痛哭,弄得博物馆的人一时不知所措。后来,顾棣把曾经装这些文物的纸袋收起来,上书6个大字:“顾棣的命根子”。
2015年,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工作人员到山西太原拜访顾棣。栗静对本报记者描述,他家有四个卧室,但每个卧室里都堆满了档案材料,一直到床边。
顾棣的档案工作让参观者惊叹不已。他家客厅有一个定制的“中药柜”,里面分类清晰地存放着他一生收藏与拍摄的八万余张照片底片。每个抽屉上,都写了大大的分类名字,“军营”“影史”“戏剧”……
对于绝大多数档案,顾棣已经想好归宿。一次聊天时,他告诉栗静,将把大多数东西都捐给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栗静回忆:“我跟他说,‘您这是落叶归根’,后来他每次都用这句话给别人解释。”
其实,这些年顾棣不断地在捐。1944年,第一版《毛泽东选集》在阜平印刷,沙飞将自己那本送给了顾棣。2015年,顾棣把它拿给纪念馆工作人员时说:“你们喜欢就带走吧。”如今,此书已成为纪念馆重要馆藏。
这不只是顾棣将资料送回家乡阜平,更是一位老兵将从晋察冀边区开始整理的档案送回这片土地。
直到去世前,顾棣在周围人眼中都像一部“活字典”。顾棣女儿顾文静告诉记者,顾棣有着惊人的记忆力。“就在他去世前10天,我问一张抗日战争时期的照片,他不假思索就能说出全部信息。”
如今斯人已去,他珍视了一生的事业也后继有人。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正与顾棣子女们商量,从今年7月开始,陆陆续续将其所藏运到馆里来,接下来希望与高校、社会各界合作,将这些资料整理好、利用好。
最终,顾棣带着底片走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天,来到了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这一年。(记者 刘少华)
《人民日报海外版》(2025年07月17日 第 05 版)
|  /1
/1 
 扫码添加微信客服
扫码添加微信客服
